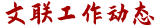郑万里:年味
儿时记忆中,过年是从杀猪开始的。
那年月生活很苦,从春到冬的饥饿和贫穷,剥蚀的人们皮里瞅肉的瘦,只有过年才会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因此,苦巴巴熬了一年的人们进了腊月就抹去了脸上的愁容,竖起耳朵仔细听着标志进入年关的猪叫声。
猪,果真就叫了。
于是,圈了一冬的孩子们再也忍耐不住屋子的软禁,一头就攮进了寒冬里,顺着猪叫的方向跑去。
临时“刑场”就设在生产队队部,这里对农民而言,关系到生活和命运,任谁也不敢小看这个十分渺小的场子。杀猪之于生产队社员,是一件非常隆重而胜意的事件。
在人头攒动的场子中间,有个两尺来高的台子,猪就在上面准备任人宰割。“刽子手”们都是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手持刀棍笑容可掬地来到场子中间,首先把胳膊抡圆喽朝着猪的头部猛地一棍,伴随着猪“嗷”的一声闷叫,一支锃亮的尖刀便捅进了猪里,只见那猪血流如注,全身抽搐,过不了一个时辰,白花花的猪肉就挂在了木架上,这场面一点也不恐怖,倒像古人征战奏凯,透着几分喜兴。
然后就分肉,分到肉的主儿脸绽得榆树皮似的,屁颠屁颠地径直往家里奔,小孩儿跟在主儿的后面,哼哼唧唧撒下一路任谁也听不懂的歌声。
这就过年了。
炸油饼、蒸豆包、包饺子、炖猪肉......都是围绕着“吃”的。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吃饱了就安居乐业,饿极了就揭竿而起,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特别是过年,人们把吃什么看的很重,因为它是对一年辛苦劳作的补偿和品味,所以宁可砸锅卖铁,也要在年下卯足了劲儿放个响屁,图的是一年开个好头儿。
过年的当口儿,除了吃,还有一项更能体现年的精髓的集体活动“守岁”。年夜饭吃罢,各种菜肴撤下,但就餐的人们不动窝,守岁开始了,一家老小围坐一起,回顾去岁得失,展望来年希望,说说孝敬老人,谈谈疼爱晚辈,其情融融,其乐融融,古人这样描写守岁:“九冬三十夜,寒与暖分开。坐到四更后,身添一岁来。”
守岁到凌晨,拜年就开始了,天刚蒙蒙亮,长辈们就备好了瓜子糖果,等待着晚辈们前来磕头。拜年最活跃的就属孩子们,不到三更天就睡不着了,他们成群结队来到老人房间纳头便拜,头磕的梆梆响,乐得老人们前仰后合,然后就发瓜子糖果,边发边说:“小兔崽子,快点长啊!”
改革开放之初,我第一次从部队探家,正赶上那年的春节,我和哥哥去给族里的“满儿爷”拜年,“满儿爷”见我和哥哥来拜年,心里十分高兴,忙招呼我们坐下,并命大儿媳端茶倒水,送上糖果,老人情不自禁地给我们唱起了“王二姐思夫”,乐亭大鼓曲调,唱得有滋有味。唱毕,老人突然问:“我怎么还不死啊?”
我们忙着劝说:“好好活着,生活很快就好起来了。”最后,我们约定等着我第二次探家再见。很遗憾,两年后老人去世了。生活的贫瘠,让老人活得不耐烦了,这种情形在那个年月并不鲜见。
拜完了家族中的长辈,接下来就是走亲访友。过去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紧着忙乎都填不饱肚子,也就谈不上平时走亲访友了,只有到了过年才相互走动走动,相互通报一下情况,算是对亲友情分的维系吧!
过了年,挂在人们脸上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于是就有人感叹:“过年不如盼年。”真的,盼年是人们心中一种升腾的希冀,过年则是贫困日子的回归。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饱胀的希望中收获干瘪的欢笑,在火热的追求中过着贫苦的生活。
好在那年月的“年”稀释了人们太多的困顿和失望。
然而,世界却充满着悖论,过去,人们的生活虽不富有,但过年却充满着浓浓的年味,人们几乎把年当做图腾顶礼膜拜。现在,人们的生活好了,年味却一年淡似一年。人们对年的感情也没过去那般浓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