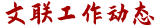张锐权:我欠母亲一声“妈妈”
我是一个喜欢诗意的人,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一山一水,点点滴滴,总能触动我心田中那最柔软的部分。常言道: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一个不会仰望星空的老师,不是一个好老师,而在星空中最璀璨的一颗星星就是诗歌。
诚然,星空中那最璀璨的星星,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为燃亮属于自己的星星,能够在星空里健康成长发光,终究在生活的大千世界里照耀生命,留下我们付出了青春与血汗的轨迹,而感到点滴的欣慰与骄傲。当中的滋味,除了酸甜苦辣咸,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让我感到为人父母,亦为人子女,我又何尝不是自己父母的孩子?念及此处,念及母亲,心中一酸,眼眶湿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出生于小榄乡村的一个农村家庭,家境比较贫穷。父亲从来沉默寡言,从小到大,他一方面为了谋生而比较少陪伴我成长,我对他心生间距,敬而远之。而母亲,天生耳朵半聋,不识字,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我付出了许多。我自小体弱多病,是母亲含辛茹苦地将我和妹妹俩拉扯大的。母亲的辛苦,母亲的爱,只有自己的孩子明白,勤恳劳动、任劳任怨的她,从来不图我们对她有什么回报。我们欠她的,何止养育之恩啊?!
记得我还未懂事的时候,大约三四岁时,有一天夏天的中午,午饭后,母亲怀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妹妹和我一起,躺在铺垫于大厅红介砖地面的席子上午睡。厅门敞开,席地而睡,这样睡午觉,任门外的南风沐浴我们朴素的肌肤,清凉地舒展我们一丝一缕的美梦,在当时的乡村农家里,是相当惬意相当满足的生活的一部分。睡着睡着,朦胧间我忽然被几声怪叫声吓醒,我睁开眼睛时,只见几头“庞然大物”在院子里正向我们走来,直吓得我大叫:“妈妈!妈妈!妈妈……”原来是邻居养的几头猪,“闯”进我们家的院子,我当时十分的害怕,想叫醒妈妈把我藏起来。可是我叫了十几声妈妈,她也没听见,我慌张地伸出小手用力去推熟睡中的妈妈,她醒了,看着慌张的我问:“这么快睡醒啦?怎么了?你慌什么?”我指了指屋外的“庞然大物”,她一看,微笑着对我说:“孩子,不用害怕,是隔壁李伯伯家的猪,我赶走它们吧,你看着妹妹一会儿哦。”她放下熟睡中的妹妹,拿了一根小竹竿,一个箭步过去,连喝带哄地把那几头肥猪赶回了邻居李伯伯家……这件事一直投影在我的记忆中,烙印在我的小心灵里。
自从那天之后,不知为何,我不敢再叫母亲一声“妈妈”,但已将母亲当成自己的保护伞,有什么难事或者害怕之事,总希望母亲第一时间在我身边,为我遮风挡雨。母亲,在我眼中既是美丽的化身,又是英雄的化身!
在我懂事之后,我才知晓母亲的耳朵是半聋的,平时叫她是听不见的,要走到她身边,大声地说话,她才能听得见。后来慢慢觉得这样的交流方式很麻烦和吃力,而且在公众场合与她这样的大声说话交谈,许多时候都觉得尴尬。随着我身心的成长,后来想到,比起她养育我们的艰辛和吃力,我们感觉与她交流的“吃力”,又算得了什么?
我十岁左右,经常生病,每次都是母亲骑着自行车载我去卫生院看医生的。有一天,在她载着生病的我去看医生的半路,我想呕吐,想叫一声母亲: “妈妈,停一下车!”可是,“妈妈”两个字刚涌出嘴唇,又溜回咽喉,吞回肚肠。于是我伸手轻轻扯了一下她的衣角,大声说:“停一下车,停一下车!”……次日早起,病好了,我便愉快地想跟母亲说我病好了。母亲正在厨房里全神贯注地做早饭,不知道我已起床,我走到她身旁,很想说:“妈妈,我的病好了,今天精神多了!”可是,“妈妈”两个字正脱口而出之时,内心有一种别扭的感觉,犹豫了两秒,又吞了回去。于是伸手轻轻拍拍她的手臂,她回过头来:“唉,孩子,这么早起床了呀,好些了吗?”我对她大声地说:“我的病好了,今天精神多了,所以早点起床吃你做的早餐!”……
轻轻扯一下她的衣角、轻轻拍拍她的手臂,一直是我跟母亲沟通交流前的一个动作,虽然“拉近了”我们生理上的距离,却在无形之间,仿佛隔远我们心理上的距离。因为母亲是明白的,我这样接触她的一个动作,代表了我叫她一声“妈妈”。这么多年来,她习惯了我的这个“习惯”。而今天,已成家立室的我,渐渐觉得这个“习惯”越来越不习惯,却依然“习惯成自然”,没有勇气去大声对她喊出一声“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