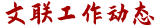章晖:落满时间的声音
落满时间的声音
章晖
对面建了一年的别墅楼,终于进入了装修期,想必装修也得花一年半载。
十月怀胎,建楼两年,关于生命的孕育,急不得。
施工之前,那块地是附近老人种植的百科园,长着诸如芝麻、花生、豆角、淮山、玉米、桑树、枇杷等,这些灵性的植物,一旦登场,将四季演绎得淋漓尽致。
别墅楼旁边是一幢日式别墅,以我来南方算起,房龄已超二十年,据说男主人很能干,自己开印刷厂,儿子有出息,父母也宽心,在屋后种菜养鸡,安享晚年。老人说一口四川话,人很随和。可养的鸡却不择时常在午夜打鸣,晚睡的我赶紧把云游的心拽回来,毕竟肉身抗不过睡眠。
突然某天看到庞大的挖掘机开到别墅院落,轰隆隆地忙乎起来,听老人说要建地下车库。但事与愿违,车库还没建好,院墙却被震出了裂缝,看来主人又改变主意,推倒院墙重建,楼上凿壁开窗重新装修,搅拌机更是泥沙俱下,忙个不停。
这可不得了,两幢楼左右齐肩并战,一个初成长,一个要改装,那欢腾的,沉重的,尖锐的,跌宕起伏的电钻声,锯齿声,敲击声混合成五音杂陈的高分贝噪音,真是苦煞了两只小耳朵。
所居处的宁静就这样被打破,它们仿佛向生活发出了持久战宣言。而我常在清晨六点多的“宣言”中醒来,在七点钟逐步升级的“宣言”中清醒,我不知道附近的居民是否与我一样,睡眼惺忪站在阳台伸着懒腰耐着性子洗耳恭听。然后像一张扑克牌,在朝阳的映照下,将自己毫不吝啬地甩出去,在车水马龙中,接受新的牌局组合。
有时我想,仅仅是两幢在建私宅楼就已影响到周遭的生活,而那些施工数年的建筑,道路或桥梁,一根扰民的弦,拉扯着多少忍耐和包容。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而声音无法称重,愉悦听觉,也摧毁听觉。如花,自开自落,雷雨,是天空之花。歌声、哭笑声,是声带之花。风无形,却让山川开出最美的花。
曾听说一个坐火车的孩子听出了火车异样的咔嚓声,从而挽救了全火车的人。
我也曾听出我开的车轮胎唱着跑调的歌,但修理师傅将耳朵贴着轮胎,听到的却是汽车修理厂的噪音。但他用眼睛、设备检测确定并无异常。
当高架桥从楼宇中央穿过,梦是否也在梦呓中加速。
我们终究生活在尘嚣之上,被各种声音分解,又分解出各种声音。
蛙声,匍匐于大地,从容而浩荡。
而我们常用温水煮青蛙来形容对所处环境的依赖,却完全忽略了潜在的危机。
虽说实验中的青蛙未识破人的诡计,但那草丛或积水浅湾里的青蛙,它们因地制宜地繁衍,辗转成大地的流浪歌手,转化成田园的赤脚医生,蓬勃的生命形态,有着我们太多的影子。
曾经在一条水泥路上看到晾晒的青蛙干,数量之多令人震撼,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腥味,晒蛙人坦然地说是朋友养的蛙用来做药引。
想起莫言在小说《蛙》中说,蛙与娃谐音,与娃有关。我们是蚁族,我们也是蛙族。有时沉默,有时发声。蚁族,面临着踩踏。蛙族,面临捕捉,其实活着本就是危险的事。
而我到底属于哪一种蛙?想想半生已过,终是一无是处,在闲暇时光里却甘愿沉潜在文字的缶中,任命运添加柴火慢慢煎煮,却并不打算跳脱。
正如此时,晨钟响起,我读到爱默生的句子“真正的船是造船者”时,泥瓦刀如藤般开始攀墙走壁,窗外,再次落满时间的声音……